本文由微信公众号环球科学ScientificAmerican授权转载。
————————————————————————————————
撰文 路德维希·西佩(Ludwig Siep)
翻译 姜艳香
西方的一些所谓的“反人类人士”宣称,人类急需改良。这些人希望尽快帮助人类获得新的特性(就像我们熟知的、只在某些机器或其他物种上存在的“超能力”),如红外线成像,或者超声波探听等,以使人体技能得到进一步扩展和加强。
实际上,借助于克隆技术和人工授精的筛选,以及对子代基因进行改良等生物技术,人类已经在“优化繁衍”这条路上取得了不小的进步。按照再生医学理论,延长生命不仅切实可行(如向人体移植动物源性的器官或组织),而且,相关的技术——例如使用更激进的基因敲除技术, 调控细胞的凋亡或其他退行性过程——有着远远超出目前水平的潜力。
另外,大脑的侵入性治疗、植入体移植和药物治疗等手段,不仅能保证医学范畴的治病效果,还能以“神经-心理-增强”的方式,提升人体的功能。而新兴的“量化生活运动”(简单地讲,就是全面监测人体活动),则可通过持续、精心地检测人体那些未知的功能,实现对人体的全面控制,最终将人工合成的外在组份应用于人体改良。
可是,我们真的需要“新人类”吗?如果需要,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我们又承担了哪些风险?这些疑问,不应该只让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实验室里讨论,所有公众都应该参与,并将其提升到哲学层面。上千年来,人类很少面临如此难题,改良行为和改良人类的定义是什么?哲学家们也在发问:当今“人类改良”的含义是什么?其中哪些改良是有益的?
自远古时代起,人类就梦想着提高自己的能力。如今,这个梦想的实现似乎近在咫尺。以生物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各种新型技术,为改变人体提供了新的可能。通过超级计算机等机器的模拟,这个梦想更加鲜活起来。人类改良的终极目标,也呼应了进化论的要求——使人类更加适应日渐严酷的生存条件。
在古代,改变身体并非人力所能企及。人们能重拾这个不曾磨灭的梦想,还要感谢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借助科学技术,我们能够对自然过程做出规律和可重复的解释。我们可以按照科学规律来制造机械工具,以满足自己的需求——这些工具的雏形在17世纪的欧洲就已经出现了。与此同时,人类也利用科学技术,一定程度地改善了人体系统的原始功能,并产生了驾驭自然的原初概念,包括提升人体功能,以及对动植物进行物种改良。在1627年出版的《亚特兰蒂斯》里,哲学家培根就曾描述过这样的乌托邦式的社会范例。
“好” 与“不好”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代,西方的经验主义社会学开始萌芽,一种新思潮由此诞生:创造一套完美的社会秩序,动用一切社会资源来提高人体的能力。紧随这种“新人类”理想的,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充斥着变革和强权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从现今主流思想的视角出发,乌托邦社会主义是一个巨大的失败。这一构想对人类道德和本能的自然属性提出了过高的要求,是以牺牲个人自由和生存条件的改善为代价的。“好” 或 “不好”到底是什么?人们对此持有不同的见解,而这一点恰恰又被忽视了。
现今,有关改良人类的议题,也面临同样的风险。生物工程师们宣称,依靠纯粹的技术手段就能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但实际上,我们真正能判断出好坏的,只有汽车、飞机、手机、个人电脑等具体的产品。通过纯技术手段就能判断“好”与“不好”,这个命题其实已倍受质疑。这不仅仅是美学概念上的区别——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天然优势,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愿望来提高手中工具的性能。对某一些群体——比如老年人——来说,要求工具的这些高性能恰恰是多余的(或者说是一种苛求)。我们尚不清楚,诸如此类的“好” 和 “不好”是否可以由政府或者市场来评判。并且,市场的导向手段绝不像选举一样,是完全合理与民主的。
由此产生的一个根本问题是: 一个优良的人类到底是什么样子?从哪些条件来判断“他”是否值得我们拥有?
治疗与改良的界限
或许,人们可以从反面来理解“好”的概念: 当人们遭受疾病的折磨时,会产生远离疾病的愿望。人们不仅要依靠自身的承受力来忍受病痛,也要依靠先进的技术来战胜病痛,这是新时代人类所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那些物质和非物质的东西,能够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治疗疾病,将人们从劳苦和病痛中解放出来,这些毫无疑问是“好东西”,这在伦理学方面也是肯定的,例如所有针对人体的人工矫正品——从眼镜、助听器和帮助行走的工具,到植入体和移植器官,都是“好东西”。
如果在装备了上述制品后,一个人在技术层面变成另一个人,这是更好的事情吗?只要想到在上个世纪早期,60岁的人就驼背、耳聋、牙齿掉光,这个答案无疑是肯定的。所有诸如此类的治疗手段,就是为了减轻个体的病痛,但绝不是为了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个体。当然,医学治疗还能够延长人类的生命,这也实现了古人的梦想。而今,诸如干细胞疗法的治疗方案,就被认为是人类未来的“不老之泉”。
治疗疾病和增强人体功能,都是为了改善我们的身体,这两种目的之间是否存在一个界限,医学伦理学界尚在激烈的争论之中。然而,即便这个界限是模糊的,对二者进行鉴别仍然具有意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出区分呢?这与我们的目的有关:我们是单纯追求人体能力的提高,还是意在去除已确诊的病痛,或者是既要消除身体疾患,又要追求身心完美?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愿望权衡利弊,而后作出某个愿望优先或者将利益最大化的决定。由于我们愿望的复杂多变性,“人体改良”还无法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规范。
当然,这里也存在一些几乎所有人都怀有的愿望——比如延年益寿,对于一个经过生物改造的人来说,这应该是可以实现的。那些为老年人的生活带来真正改善的“好东西”,也是值得拥有的。但是,如果人的寿命真的可以延长,那么,我们就应该毫无保留地支持相关的技术和做法吗?
在对这些问题作出评价前,首先应弄清以下问题:对于延长寿命,所有人都能平等获得这样的机会吗?这与自身经济状况等社会属性无关吗?如果不是,那么“人人平等”这个命题,会被多大程度地削弱?社会的贫富差距又要增大多少?大量高龄化人群,将要耗费多少自然资源?土地和未来的高科技能够从容应对吗?这会不会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自然风貌被侵蚀、农作物产量下降?在人类世代更替的过程中,又会出现哪些问题?
为了实现改良人类的目的,同时在地球有限的生存空间中,适度、可持续地长期利用资源,那么人类首先必须要控制生育。这样一来,我们这个星球上年轻、富有创造力的人群势必会减少。这样的“社会进步”值得我们拥有吗?
在这里我既不能,也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在生物工程师们开展“新人类项目”之前,整个社会对于“好东西”的概念,以及“改良人类”的进一步目标,应当展开一场讨论,同时还要考虑到所有不同的观点,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都要参与讨论。
但凡讨论不出来一个确切的结果,我觉得,人们就应该暂时放弃急躁激进的“新人类”培育方式。借助于医学治疗和良好的卫生、营养、空气等生存条件,我们应该谨慎地对人体进行改良——让我们有一个共同思考的空间,避免那些无法挽回的错误决定。
本文作者 路德维希·西佩是德国威斯特法伦-威勒海姆大学哲学系教授,他长期关注现代生物技术的研究和进展。他主张,“改良人类”的标准不能由工程师和各种技术、工具的生产商制定,而是应由公众进行广泛讨论得出结果。
本文译者 姜艳香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预防医学专业,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信息管理专业获得硕士学位,目前任职于德国海德堡大学医院某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环球科学ScientificAmerican,经授权发布,转载请联系环球科学ScientificAmerican(微信号:huanqiukex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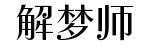 解梦师
解梦师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