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从来不是记录在胶片上的电影,一成不变,它是一个只有目录的故事,随着每一次的讲述,由讲述人——我们自己——根据当时的情况,重新丰富它的内容。
“明明记得就在包包里啊……”
从小到大每次找不到东西之后,妈妈总会像变魔术一样从另一个地方找出来,用事实推翻了你的“明明记得……”,有时你甚至觉得这是针对自己的恶作剧,因为所有这些记忆都太真实了。
记忆,你给自己编的故事
很少有人怀疑自己记忆的真实性。1993年被心理学家汉斯·克劳姆巴格(Hans Crombag )和同事们调查的人们也一样对自己的记忆深信不疑。但他们当中有一半以上都错误地“记得”十个月前,1992 年 10 月4 日,一架波音747飞机撞上阿姆斯特丹一栋大楼的情景,并且还能生动地描绘飞机撞上大楼的全过程。他们以为自己在电视上看到过这些画面。而事实是,没有任何人拍摄到了这起事故发生后一个小时内的现场录像。
无独有偶。1996年7月17日晚上8时30分,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800号班机在起飞12分钟便坠入大海。其后,有目击者声称看到有导弹击中了飞机。这样的说法在媒体上传播。有些人坚信这架飞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安全的飞机,出故障的概率很小,更可能是被导弹摧毁了。而在之后的调查中发现,这些人也报告称自己在电视上看到了导弹撞向飞机的镜头。
难道是我们对于公共事件的记忆更不准确吗?
其实,对于我们最关心的自己,记忆似乎也没有更“忠实原着”。
你还记得2008年5月12日下午在干什么吗?你很可能还清晰地记得,因为那一天对于你来说太不普通了,一定会印刻在脑海中永生难忘。但是如果有办法可以验证,现在的记忆和当时真实发生的故事,也许非常不同。
事实上,“9·11”之后的美国人就是如此。在“9·11”之后的1周、6周和32周时间里,美国的心理学家对美国7个城市的居民进行的抽样调查发现,尽管他们自以为对“9·11”当天保留着清晰的记忆,但是他们这几次的问卷中,却存在着大量的自相矛盾的地方。最有意思的是,他们相信自己“现在”的记忆更准确,而上一次离事件更近时的记忆反而“不够真实”,就好像脑中有新的、更准确的记忆又被唤醒了。
记忆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有个段子,一个天然呆妹子梦到自己向暗恋的男生表白,男生同意了。第二天起床以后分不清梦境和回忆,看到此男就各种招手各种欢笑各种凑上去红着脸牵手。此男一脸茫然,后来也就默认两个人好上了。
在嘲笑这对天然呆情侣档的同时,请不要以为自己不够“呆”。分不清现实和虚构不是智力问题,很可能是过剩的想象力在作祟。想象力丰富的人大脑里存贮着更多的脚本,当现实中发生的某一幕和脚本合拍,有时就会被大脑解读为“往日重现”、“似曾相识”。
电影《盗梦空间》也借鉴了这一现象:梦中的情绪会代入现实。里昂那多扮演的盗梦者不但可以从人们梦境中窃取秘密,还可以将一些虚构的信念通过梦境植入人的意识当中。
分不清真实和虚构,并不仅仅存在于科幻或段子里。只是普通人大多没有机会验证自己的记忆,所以对因此盲目自信也不会对生活造成太大影响。但对于公众人物,这样的记忆问题却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声誉。
里根在1976年到1984年竞选的时候,喜欢不厌其烦地宣讲一则发生在二战期间的感人故事:一架轰炸机被导弹击中,年轻的士兵吓得尖叫起来。年长而睿智的指挥官勇敢地安慰道:“没关系,我的孩子,我们一起飞行到底。”里根每次热泪盈眶地讲完故事后,还会不忘告诉大家,最后这位指挥官被授予国会荣誉奖章。
奇怪的是,里根为何对两名战士的对话了如指掌?一名记者也许也提出了同样的疑问,他好奇地查找了所有434位二战时被授予奖章的军人,并没有找到里根描述的这个指挥官,反倒是在一部电影中看到了类似桥段,飞行员最后也对战友说:“我们一起飞行到底。”而白宫则一直把这个故事当做真事。当记者对白宫提出质疑后,白宫内部发生了一场争论——他们也想知道,里根总统到底知不知道自己讲的是虚构的桥段?
虚假记忆猛于虎
中国人向来对人的记忆能力持宽容态度,认为“贵人多忘事”,但在法律面前,“难得糊涂”毁掉的,可能是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
乔治·富兰克林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在51岁的时候“晚节不保”,被女儿告上法庭。理由是乔治的女儿伊琳想起20年前,1969年9月22日,亲眼看见爸爸把她最好的小伙伴苏珊·内森奸杀。之所以20年后才提起上诉,理由是这段记忆太不堪入目,以至于深埋在了小伊琳意识的最深处。直到最近的心理治疗才唤醒了她最深处的记忆,伴随着一次次的记忆闪回,伊琳渐渐拼凑出了父亲犯罪的完整情节。
陪审团没有怀疑,毕竟谁会无缘无故翻出二十年前的陈年老账冤枉自己的生父呢?当事人的亲眼所见还不足以作为最有利的证据吗?1990年11月29日,乔治·富兰克林被判处一级谋杀罪。
面对陪审团,认知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拉夫特斯(Elithebeth Loftus)的证词当时却显得不是那么“顺耳”。作为记忆研究的权威,拉夫特斯致力于研究错误记忆(misinformation memory)。她通过各种精巧的手段提供干扰信息,左右人们的记忆。
她发现,甚至只一个用词,都可能影响人们的记忆。即便是看过同一段交通事故的录像,如果是被问及“两车相撞时车速是多少”,人们对记忆中汽车速度的判断就会明显大于被问及“两车剐蹭时”的速度。在用到“粉碎”(smash)这样强烈的词汇时,有的实验参与者还回忆出了玻璃破碎的画面,而实际上录像中并不存在。但如果使用“剐蹭”(contact)这样的词汇,参与者就不会回忆出严重的画面。也就是说在实验中,拉夫特斯可以通过改变询问所用的词汇,而将不存在的画面植入到参与者的记忆当中。
由于拉夫特斯所做的记忆研究,她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收到了上百封求助邮件,内容怵目惊心。然而它们都讲述了类似的故事,一个人忽然接到法院传票,理由是子女在经过心理咨询之后回忆起童年被性虐待和乱伦的经历。凭着拉夫特斯对记忆的理解,记忆不是录像,不能客观地记录历史,她认为,不可以仅凭一个人的记忆就判处另一个人有罪。
但陪审团不认为拉夫特斯这些诸如汽车玻璃是否破碎之类的针对细节的实验能够和奸杀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记忆可以不准确,也许可以增减些细枝末节,但要想将如此重大的伤害性事件无中生有,生生植入记忆,简直是天方夜谭。
陪审团的判决让拉夫特斯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促成她做出了改变人类对记忆认识的伟大研究。
记忆植入不是幻想
很多年前的一则高考作文题目便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移植记忆听起来总让人感到有点科幻。但其实记忆移植每天都在我们的脑海里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只是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除非一个偶然机会,让这种植入被记下并公诸于世。
着名发展心理学家皮亚杰曾经一直以为自己最早的记忆是在2岁左右,因为他清楚地记得那时候襁褓中的他差点被劫匪绑架,幸亏他的保姆英勇地和劫匪搏斗,为了保护皮亚杰,保姆身上还有好几处被抓伤。这画面一直清晰地储存在皮亚杰的脑海里,直到15岁时收到保姆寄来的道歉信,告诉他这件事纯属虚构,只是想让皮亚杰一家能够对她心存感激。
如果不是保姆主动坦白,恐怕皮亚杰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被植入了一段记忆。
是不是因为皮亚杰年龄小,所以记忆也比较容易受到控制呢?
拉夫特斯对年龄跨度更大的人们展开研究。为了说服对记忆移植抱有疑虑的陪审团,她必须给人们植入一段完整的故事,这个故事还必须有一些伤害性,植入故事的人必须是当事人信任的权威。
为此,拉夫特斯设计了一个在超市走丢的故事。她让实验参与者的亲属给参与者讲故事,其中几段是参与者小时候真实发生过的故事,在其中夹杂其实从没发生的“超市丢失事件”,再让参与者判断是否记得以及能够回忆多少细节。拉夫特斯发现,经过几次暗示之后,四分之一参与者都被植入了超市走丢的记忆,反倒是一些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他们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后来拉夫特斯又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凭着这些研究她终于说服陪审团重新考虑那些宣称曾经被抑制记忆的证人的证词。
记给未来的自己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记忆都是现在的认知。没有人能站在过去的角度看待过去,每一次回忆都戴着一个叫“现在”的有色眼镜。
社会心理学家卡罗尔·塔瑞斯写过:“记忆就像生活的目录,有了它,我们就不用每次都从头生活一遍。”
一方面,不妨从现在开始,有意识地记录一些美好,也许未来会用得着这些记录,给善忘的自己,再次植入些充满欢笑的回忆。
另一方面,在翻开记忆之书时,我们也不用总是“打开的方式不对”——比如不要选择性地调取那些痛苦的记忆。不妨有意去选择美好的篇章,让那些曾经的烦恼,都变为人生里一次为了成长而接受的考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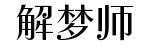 解梦师
解梦师
最新评论